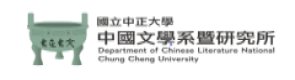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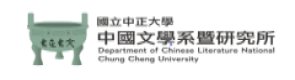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眾所周知,梁啟超提出了「詩界革命」,用詞為頗驚目光,但其實只有「維新」。胡適謀的白話文學,白話追求不只文適的零度,雖僅以論議名之,從「嘗試」開始,「要鬚作」詩如作文」之句卻絕對是讓詩篇重新翻開新頁,「詩國革命自此始」。經此,舊詩雖已創作,雖不能說是屍居餘氣,但被稱為骸骨迷戀,也不是善意的稱呼吧。
事實上,舊詩本身並非抱殘殘守缺、食古不化,晚清黃遵憲提出的離合伸縮之法,樊增祥強調「光景日新日奇」,因生新詩境;沈曾植提出的三關說、易順鼎以七言歌行表現新事物新感覺的詩歌實踐、吉川幸次郎從陳三立詩中書寫的「現代的」感覺、錢鐘書敏銳的解讀出王國維舊詩裡的現代時間感等,無一不是對當下、當下的積極回應,他們的詩學體現出了的轉變,既是「微妙的革命」,更不凸顯的現代性。
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,在政治高度不正確下,而這個被視為廢棄物的遺老們,「詩歌是危急狀態下的語言」,他們卻擁有最深刻的詩學實踐,雖然這樣的「新」詩學方案,是百年沒有人思考的答案。這樣的「潛蛟之舞」的意義可以重新重新檢視,或是能夠給當代的我們進一步思考文學何用、詩歌何為?以及,對於什麼形構了「現在」、「過去」又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其中,提供當代歷史縱深的一些思考。
